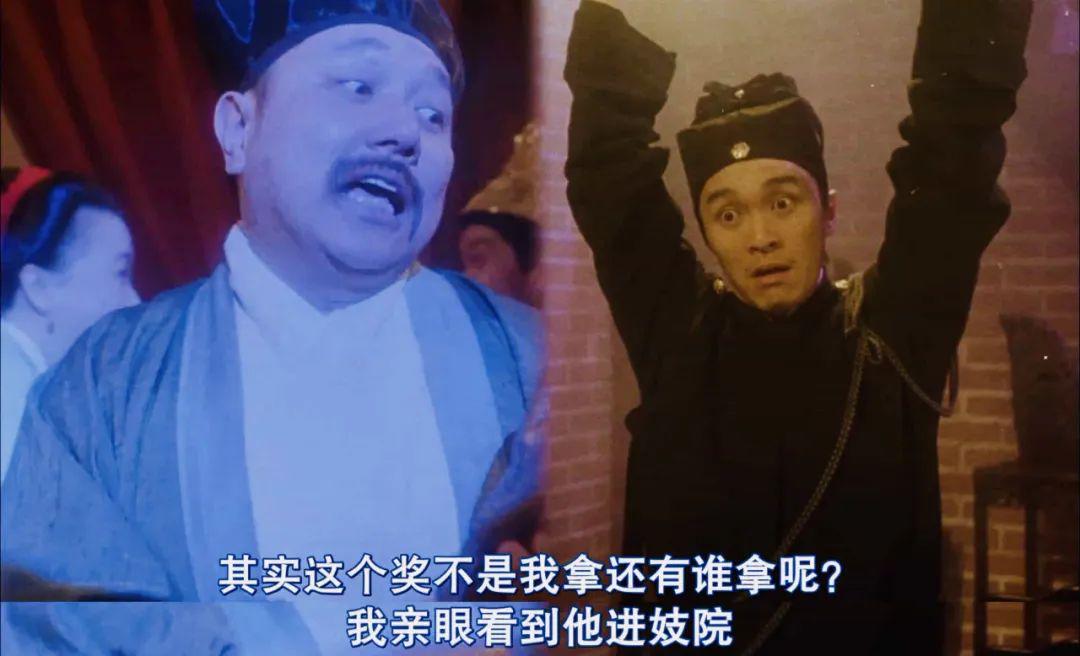
文|李宇琛华融资产
在成都的江湖里,老一辈的规矩叫“袍哥人家,绝不拉稀摆带”。
意思是,要讲义气,不掉链子。
2008年,人类学博士张原带着老婆一头扎进成都时,还以为象牙塔里也是这个规矩。
那时的成都,空气里还可以飘着火锅底料和新思想的混合味道。
张原夫妇是天降的“顶配”:双双人类学博士,名校师承,牛津履历,还带着一身田野故事。
他们很快成了成都文化圈的吉祥物,组了个“原汤抄手”家庭乐队,唱着自己写的歌。
中产们在朋友圈转发他们的视频,配文是:
这才是理想生活。
在西南民族大学民社院,他们也被视为未来的希望。
学生们觉得,这对夫妻学者,学术扎实,生活有趣,浑身散发着理想的光芒。
张原当时不会想到,这种光芒,有时候特别:
招黑。
他更不会想到,他即将遇到的那位学院学阀,最擅长的事情,就是把别人的光,吸进自己的黑洞里。
这位领导叫蒋彬,后来成为民社院的院长。
公开资料说他研究城镇化,私下里老教授们说他研究“人”。具体来说,是:
研究领导。
他的主要课题,在酒杯里,在麻将桌上。
至于书斋,那是课题结项后用来摆拍的地方。
蒋彬教授 的学术成果,大部分被引量是0。
他被引用最多的一篇论文,二作是张原,一作的 蒋彬 只是挂了名:
这几乎是蒋院长整个学术生涯里离学术最近的一次。
对蒋院长来说,学术是向上爬的梯子。
而像张原这样的青年学者:
就是梯子本身。
刚来的张原,自然要“拜码头”。
帮领导写本子、挂名发论文,都是基本操作。
张原甚至有机会,手把手教这位博导如何写一篇规范的论文摘要。
蒋彬教授 的算盘,珠子很快就拨到了学术圈外面。
2009年,他拉着张原开新车上山搞项目,大雪封山,车坏了。
张原自掏腰包把车拖回成都。
蒋教授或许觉得,你能为我的项目出车出力:
是你的福报。
汤芸通过师门关系,从乐施会拉来30万经费。
蒋彬教授 眼睛一亮,伙同另一位老教授轻松截胡。
项目组里塞满了他的“朋友”:
经费怎么花的成了一笔糊涂账。
这笔账华融资产,最后落在了张原夫妇头上。
几年后,学校财务处通知他们名下有16万借款逾期。
一个他们只经手了不到3万的项目,留给他们一个长达15年才填平的巨坑。
那一刻张原夫妇才明白,在这个学术江湖里:
“袍哥”是传说,“拉稀摆带”才是日常。
他们决定,离这伙人远点。而这个决定,让他们从“梯子”变成了“钉子”。
每个山头,都需要一个冲锋陷阵的打手。
梁艳博士,就是蒋院长最趁手的那一把。
梁博士的专业是藏学,但她在学院里更出名的,是她的:
斗争学。
她能把自己的研究生当家奴用,骂到学生去看心理医生;也能用“课程思政”的专项经费,频繁请学生吃饭:
把饭局变成情报收集站。
当张原在工作群里质疑她滥用经费时,梁博士理直气壮地打出了一行字:
张原老师恐怕不知道我每年请学生吃饭都要花至少万把块吧~
她似乎觉得,自己用公款请客吃饭的行为,是一种更高级的“思政”。
在那一刻,她一定觉得自己深刻领会了“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”的精髓。
这种战斗力,让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青年学者开了眼。
在一场学术论坛上被梁博士无端羞辱后,这位年轻人没忍,写了一封公开信群发民社院,措辞像一把淬了火的柳叶刀:
您以权威的假象拉踩后辈……令人不禁怀疑……是否因积累了某种深层的不如意,才导致您展现出如此不堪的姿态?您的学术贡献平平……以这样的资历,对后辈的研究全盘否定,只会显得缺乏风度且自暴其短...在继续做学问之前,或许您可以先试着学做人。
这封信成了学院师生手机里的地下文献,但没能给梁博士造成一丝划痕。
有蒋院长的保护,这些不过是蚍蜉撼树。
她可以上一秒在群里威胁张原“我一定连本带利如数奉还”,下一秒就因为教学事故贱兮兮地叫他“张院”求帮忙;事后,再甩一句阴阳怪气的“劳您费心了~”。
这种切换自如的嘴脸,是一种:
核心竞争力。
一次饭局上,梁艳听说一位同门师姐想调来,当众造黄谣说人家是:
公交车。
汤芸听不下去出言制止,一旁的蒋彬教授 却听得津津有味,非要她细说。
那一刻,张原夫妇意识到,蒋彬找到了他合用的打手。
而自己,也彻底掉进了猎物的名单里。
真正的风暴,起于一首歌。
2022年9月,贵州高速上一辆xxxx侧x,xx人遇x。举x悲愤。
被x控在成都家中的贵州人张原,用方言写了首民谣,《殇·不要问》:
不要再问那辆大x在哪里,我们都坐在那车里……
朋友配上电影画面发进微信群。这张网,从此刻开始收紧。
和这首歌打包,一份完美的举报信被送了上去,包括:
之前梁艳收集的各种“张原言辞犀利”的材料。
最后的结论是:
思想滑坡华融资产,言论不当,触犯了政治纪律。
一纸密函发往西南民大。即将退休的书记首要任务是平安落地,他不可能为了一个青椒去挡枪。
张原问能否调走,书记告诉他,密函要进档案,政审这关你过不去。
你哪里都去不了,等着学校调查处理再说吧。
这是体制内最温柔的死刑判决。
一扇门,彻底关上了。
另一边,蒋彬和梁艳的门,打开了。
围猎开始了。
张原被禁止一切教学科研,留党察看两年。他成了一只笼中困兽。
很快,一种比行政处分更古老、也更有效的武器被部署了:
谣言。
关于张原“性骚扰多名女学生”的故事,开始在各种学术圈子里流传,源头都指向了梁艳博士。
一篇网文绘声绘色,说他“抓着女学生挨个骚扰”,用词像茅坑里的石头。
脏水一旦泼上,就很难洗清。
无论你如何自证,总有人宁愿相信那些更刺激、更符合他们对“知识分子”想象的剧情。
这是对一个人社会性生命的精准狙杀。
张原夫妇不是没想过反击,但他们有软肋。
那些真心追随他们的研究生,还在蒋彬和梁艳的手里。
毕业证和学位证,就是悬在学生头上的两把剑。
江湖上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:
想拿捏一个人,就从他软肋下手。
为了学生,他们只能忍。
但麻烦还是会主动找上门。
2024年,梁艳在一个田野培训中:
把学生一个个叫进房间,恐吓盘问,翻看手机,试图罗织汤芸泄露考研真题的罪名。
一个学生在微信上向汤芸求救:
汤老师,梁艳老师不停的找我们聊天搜集付款截图等资料,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?我们说这件事很正常还被她骂了一顿……
这件事,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们决定离开。
2024年夏,他们办完离职远赴海外。张原后来写道:
我失去了太多,但最终发现,我失去的只是枷锁!
但江湖的规矩是,斩草要除根。
你人走了,影响力还在,这会让某些人睡不着觉。
2025年1月,他们受邀做了一场线上分享,隐晦提及了出走的原因。
朋友们发文纪念,称他们是:
天真的人类学家。
这份来自民间的体面,显然又刺痛了某些人。
新一轮更恶毒的谣言袭来,甚至点名道姓地诅咒他们年少的儿女:
祸不及家人。
这条江湖最后的底线,被踩得粉碎。
张原终于明白,战斗,退无可退。
他要等的,只是最后一个学生拿到毕业证的日子。
在檄文的最后,张原挑明了这场围猎的真正动机。
那不是一首歌,也不是什么思想滑坡。
所有的血雨腥风和思想之争,到头来,都可以被简化成一个朴素得令人发指的动机:
蒋彬院长的孩子想要个编制。
2021年,民社院院长空缺,业绩突出的张原是热门人选。
这个风声,让当时已57岁的蒋彬坐不住了。
他的女儿正在读博,未来的路, 蒋彬教授 已经为她在民社院里铺好了:
张原的存在,是他女儿康庄大道上最大的路障。
于是,举报和构陷开始了。
张原倒下后,超龄的蒋彬,不合常规地坐上了院长的位子。
学校领导大概认为,在驾驭人际关系这门真正的“社会学”上,蒋院长早已是超纲的博导了。
上台后,蒋院长开始为女儿运作。
张原指控,为了将女儿送到川大读博,蒋彬特招了一名川大博士来学院入职:
作为交换。
2025年6月22日,张原指导的最后一批学生,顺利拿到了双证。
第二天,他的公众号发布了那篇近两万字的檄文,标题中写到:
再无后顾之忧,可以决绝战斗了。
他把所有证据一一附上,像一个严谨的学者在呈上他的论文。
如今,成都的茶馆依然喧嚣,玉林路的小酒馆里,歌声也从赵雷换成了新的网红。西南民族大学的官网上,蒋彬院长的介绍一如既往地光鲜,梁艳副教授的课程也照常开设。太阳底下,并无新事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诠释了什么叫:
存在即合理,让你不存在,更合理。
张原和他的“原汤抄手”乐队,像一缕飘散在成都上空的烟,成了朋友们酒后谈起的一声叹息。
他曾想用人类学“保卫社会”,最后却发现,连保卫自己书桌的安宁,都需要付出全部的代价。
那个唱着《殇·不要问》的学者,和那个被举报、被污名、被放逐的“问题分子”,是同一个人。
很多年前,一位诗人写道:
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
现在看来,墓志铭都成了一种奢望。高尚者甚至来不及拥有它,就已经被迫远走海外,成为一个遥远的符号。
在这场漫长的围猎中,最吊诡的地方在于,张原在信中说,他失去了枷锁,得到了自由。这让我想起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那句台词:
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,它们的羽毛太鲜亮了。
可电影之外的现实是,鸟儿或许飞走了,但笼子还在,甚至变得更坚固、更精致了。
而制造笼子和看守笼子的人,因为又一次成功地驱逐了一只不听话的鸟儿,而获得了奖赏和更多的饲料。
他们继续在自己熟悉的道路上正确地前进着,毕竟,在一个很多人都享受有病的时候,唯一坚持说自己没病的人,才是最危险的病人。
写于2025年6月24日
我的微信:LEELOVEPHOEBE
我的邮箱:lixunhuang@protonmail.com
lixunhuang1996@gmail.com
九龙证券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